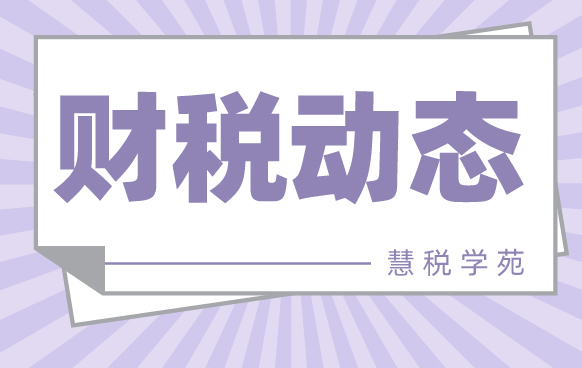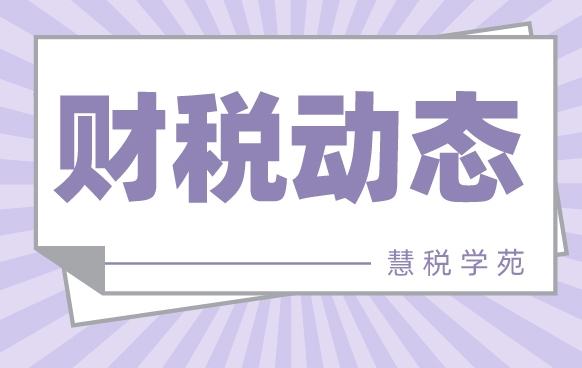从特朗普宣布对全球普遍开征的所谓“对等关税”来看,美国征收的关税已经不完全是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上的保护关税,其性质带有明显的财政关税的色彩。
从特朗普宣布对全球普遍开征的所谓“对等关税”来看,美国征收的关税已经不完全是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上的保护关税,其性质带有明显的财政关税的色彩。
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了所谓的“对等关税”方案,将“关税大棒”挥向了全球。
特朗普曾说过,他最喜欢的词语就是“关税”。在他二次执政重返白宫后的不到3个月内,就多次挥舞“关税大棒”砸向进口的钢铁、铝、小汽车等产品,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20%的关税,并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美墨加贸易协定”适用范围以外的产品加征25%的关税。
当地时间4月2日,特朗普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对等关税”方案:一是对各国至少加征10%的关税;二是根据公式计算出各国需要加征的具体税率,如柬埔寨49%、越南46%、泰国36%、中国34%(4月7日,特朗普威胁进一步加征50%关税)、韩国25%、日本24%、欧盟20%等。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高度依赖所得税筹集财政收入的国家,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收入的比重超过50%,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平均值仅为35%。根据财政学的基本理论,过高的所得税对企业和个人的投资以及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都有较大的抑制作用,不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特朗普将经济政策目标设定为大力吸引投资,促进产业资本和制造业回流美国,从而提高就业率,减少对外国产品的依赖,缩小贸易赤字,提高整体经济效率,因此特朗普在二次入主白宫前的竞选纲领中提出要继续削减所得税,主要内容包括:延长第一次执政后实施的减税计划(包括将公司所得税税率从35%降为21%等),并将制造业的所得税税率进一步下调至15%;扩大联邦个人所得税的州和地方税额扣除上限;取消或降低对小费、加班费、基本养老金等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允许纳税人购买国产汽车的贷款利息税前扣除。
这些减税措施虽然能增加企业和个人的实际收入,但会导致联邦政府的所得税收入大幅度下降。据美国负责联邦预算的委员会估计,如果不出台相应的补救措施,未来10年所得税将至少减收5万亿美元,预计到2035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负担率[债务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将提高到130%以上。而2024年美国联邦的债务负担率已经高达123%;债务利息支出已经占GDP的3.1%,占全部联邦支出的13%,其与国防开支一道成为仅次于健康保险支出(24%)和社会保障支出(21%)的第三大支出。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估计,即使不考虑特朗普的减税计划,2035年联邦利息支出占GDP的比例也将达到4.1%,2031年利息支出将达到联邦总支出的15.6%。
在“债台高筑”的背景下,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如果还想大幅削减所得税,必须找到替代税源。但美国联邦政府手里又没有增值税等普遍征收的流转税,其对“烟、酒、油、车”征收的消费税仅占联邦收入的2%—3%,根本挑不起补充税源的“大梁”。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不得不把宝押在关税上面。
关税属于间接税,其全部或一部分税款要加到进口产品的价格中由最终消费者负担,这一点与增值税或销售税相同。关税的征收面越广,适用的国家越多,其收入效应越类似于普遍征收的增值税或销售税。至于关税能否全部转嫁给进口国的消费者,则取决于产品的供求关系以及价格弹性等因素。一些美国经济学家认为“对等关税”最终不可避免要由美国消费者买单,美国众议院新民主党联盟也认为“对等关税”是联邦政府课征的一种全国性的销售税,其税负要由美国家庭承担。但特朗普政府显得格外自信,认为美国国内市场大(贸易赤字已达1.2万亿美元),出口国供应商的供给弹性小,关税不可能转嫁给美国的消费者,美国完全可以通过打“关税牌”来弥补减税造成的收入损失。从特朗普宣布对全球普遍开征的所谓“对等关税”来看,美国征收的关税已经不完全是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上的保护关税,其性质带有明显的财政关税的色彩。特朗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最近就向媒体透露,他期待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能在未来10年给美国带来6万亿美元的关税收入。纳瓦罗的这一番话,道出了特朗普挥舞“关税大棒”的另一真实目的。
然而,特朗普挥舞“关税大棒”真能如愿以偿吗?笔者认为,100年前胡佛总统用关税壁垒保护美国经济的失败教训足以说明问题。20世纪初美国开始从保护贸易转向自由贸易,关税税率也随之下降,1913年美国将工业品进口关税的平均税率从44%降为25%。为了替代关税在税制中的主体地位,美国联邦政府于1913年正式征收个人所得税,并在以后不断提高个人所得税税率,一战结束前的1918年最高一档税率甚至高达77%。如此之高的个人所得税严重损害了个人投资和工作的积极性,所以一战结束后美国马上下调个税税率,1929年最高一档税率已降至24%。1929年美国爆发史上最大经济危机,失业率超过20%。为了保护美国的工业以及就业,1930年6月胡佛签署著名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案》,重新走向贸易保护主义,对2万多种进口产品加征关税,平均关税税率从1929年的40.1%提高到1932年的59.1%。美国的高关税立即遭到了贸易伙伴的报复,也阻碍了美国对其他国家的进出口贸易,1929年—1934年美国对欧洲的出口下降了67%,从而进一步加重了经济衰退。与此同时,经济下滑造成联邦财政状况不断恶化。为了平衡预算,胡佛不得不依靠个人所得税筹集财政收入,1932年个税最高税率又一下子从25%提高到63%,进一步沉重打击了美国经济。
100年后的今天,特朗普再次向世界各国挥舞“关税大棒”,笔者认为,无论其目的如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其政策结果大概率会重蹈胡佛的覆辙。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方案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立即严厉批评美国的这一关税政策,并表示如果谈判失败欧盟将采取坚决的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卡尼宣称采取对应措施反击这种关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指出美国将为这种不公平的关税付出最沉重的代价。特朗普这次抛出的所谓“对等关税”主要涉及近60个国家,显然在世界上已经引起了“众怒”,一些国家正在研究对应的报复措施,也有一些国家担心事态扩大,试图通过谈判祈望美国降低对自己课征的关税,但这次特朗普加征的是财政关税,通过谈判息事宁人的想法恐怕最终会事与愿违,一场全球的关税大战将难以避免。3月28日,美国经济分析局也发布一组数据,消费者支出和通胀率都不及预期,美国经济学家认为特朗普的“对等关税”将导致美国经济出现滞涨。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不赞成特朗普的这种霸凌行为,美国的“关税大棒”终将砸到自己的脚。
作者:朱青(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财税研究所首席教授)

相关推荐
-
增值税法即将施行,实施条例有望尽快出台
增值税法共6章,包括总则、税率、应纳税额、税收优惠、征收管理、附则,增值税法保持现行增值税税制框架总体不变以及保持现行税收负担水平总体不变,但也有一些调整。增值税实施条例(意见稿)包括了总则、税率、应纳税额、税收优惠、征收管理、附则等六章五十七条内容。
-
税务合规管理营造法治公平税收环境
近年来,税务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持续深化依法治税、以数治税、从严治税,一体推进查处违法、优化执法、促进守法、保护合法,以税务合规管理努力营造让合规经营者获尊重、让依法纳税成常态、让违法违规者受惩戒的良好氛围,着力为高质量发展营造法治公平的税…
-
泰国前总理他信被判补缴百亿税款
11月17日,泰国最高法院就一起牵涉前总理他信西那瓦的巨额税务案件作出终审判决,判定他信及其家族成员需为其在19年前的一桩旧案补缴高达176亿泰铢(1元人民币约合4.53泰铢)的个人所得税、附加费及逾期利息。
-
破解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最高法发布一批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7个人民法院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典型民商事案例,内容涵盖融资环境优化、股东有限责任激活、历史遗留问题处置、企业名誉信用保护等多个方面。